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,人们在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杂居,以及“拟态环境”对文化空间的重构,导致了知识在获取、存储、交流、再生产等诸多环节发生深刻变化。如何面对由此带来的挑战成为摆在广大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。 大数据时代首先带来了传播话语权的迁移。在印刷时代,知识分子常常是报纸书籍等纸媒话语权的拥有者。比如,民国时期的《新青年》、《新 潮》、《语丝》、《晨报·副镌》等报刊,其编者常常具有大学教师、编辑、作家等多重身份,这为他们重构文化空间、进行文化启蒙打下了重要基础。而在大数据 时代,由于媒介身份和教育身份的分离,当今学者难以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权。文化话语权逐步从传统学者移至媒介巨头,尤其是以电视、网络等现代传播手段 为代表的传媒机构。无论如何,大数据重构了文化传播的空间形态,也打破了原有的话语体系平衡,缔造出新的话语权分布,进而带来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:作为 掌握媒介话语权的传媒机构如何重塑文化价值空间?从目前看,媒介文化产业正迅速崛起、快速发展,但由于从业人员的芜杂,资本力量渐渐成为传媒文化的主宰。 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,文化的价值向度被严重剥落。不仅如此,媒介偏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印刷文明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,同时鼓励严肃、有序和具有逻 辑性的公众话语。而大数据不仅用视像渐渐取代传统文字,还使信息变得海量且混杂无章,这导致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。正如尼尔·波兹曼的喟叹:这是一个“娱 乐至死”的时代。因此,在大数据时代,广大学者必须积极应对文化空间和教育背景的深刻变化,特别要处理好“为学”及人文教育等问题。 首先,就为学而言,在印刷媒介时代,藏书、购书与纸媒阅读常常是文人学者为学的主要方式。民国时期,学者家中的藏书一般都要超过上万册,据 邓云乡回忆:“教文史的大教授通常都藏书几万册”。“据统计,现存鲁迅藏书有4062种,约14000册,其中中文书籍2193种,外文书籍1869种, 包括中文线装书、中文平装书、俄文书、西文书、日文书等。”可以说,鲁迅的文学及学术成就与其藏书、借书乃至抄书密不可分。而在知识的交流与传承上,也多 是通过课堂、宴饮、聚会、拜访等方式进行。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,林徽因的“太太客厅”、朱光潜的“读诗会”、《晨报·副镌》“沈从文们”的聚会等 都是当时为学交流的典型代表。 而在大数据时代,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查到各地的藏书状况及学习资源,国内外开放的网络数据资源使知识获取更为便捷迅速。数字化出版的崛起更 是重新塑造了人们的交流方式、交流对象和文化传递模式。在知识的存储上,电子图书具有纸媒所不具备的携带方便、易于查询等长处,实现了从古昔的汗牛充栋到 当今的大容量可移动介质的重大转变。在知识的交流上,网络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机会,E-mail、博客、微博、论坛、微信等网络平台已经成为日常交流 的重要方式,而知识的分享、交流和传递也更为迅速和便捷。在知识的再生产上,海量网络资源为人们的书写记录提供了重要平台。比如,部分史料在搜集、整理、 编写、保管、出版、传播等环节开始趋于数字化发展。由此可见,大数据时代的“为学”方式较纸媒时代已经发生很大改变。随着“数字鸿沟”的不断拉大,广大学 者除了要秉承传统的为学精神,还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获取及交流方法,使自身的学术研究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。 此外,人文教育也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。30年前,尼尔·波兹曼在谈到电视对美国教育的影响时指出,“美国目前最大的教育产业不是在教室 里,而是在家里,在电视机前。”这种警醒亦如当下的大数据之于教育。传统课堂传授的知识备受各类现代传播媒介的信息冲击,学生获取知识及价值认同的途径已 发生重要改变。大数据时代使得我们的教育变得越来越“教条化”。这就要求人文教育工作者既要注重网络传播的伦理规范,还要加强高校自身的职责建设,推动网 络新媒体与传统教学资源的有机组合。 舍恩伯格和库克耶在《大数据时代:生活、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》一书中指出,“大数据”正像冰山一角,其价值与影响远超出人们的想象。20世 纪初,印刷业的发达,稿费制、新学制的建立,新文化运动的发生,使人文知识传播与教育发生了重大变革,而当今的大数据浪潮又使其重临新的机遇与挑战。广大 学者更要顺应时代要求、发挥自身作用,不断推动人文价值力量参与文化空间重塑,不断扩大人文学术的话语权和影响力。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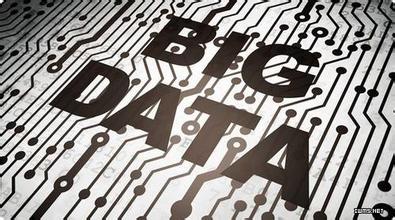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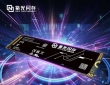



 /1
/1 

